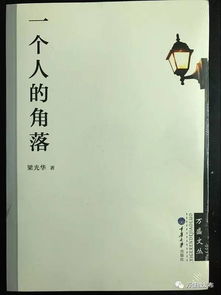在中國(guó)現(xiàn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的星空中,許多作家不僅是創(chuàng)作巨匠,更是閱讀的踐行者與布道者。他們關(guān)于讀書(shū)的見(jiàn)解,往往穿透紙背,直抵文藝創(chuàng)作的核心,為后來(lái)者點(diǎn)亮一盞盞明燈。
魯迅曾說(shuō):“讀書(shū)如蜜蜂采蜜,倘若叮在一處,所得就非常有限。”這句話道出了閱讀的廣度與創(chuàng)作視野的關(guān)系。魯迅自身的創(chuàng)作涉獵小說(shuō)、雜文、翻譯等多個(gè)領(lǐng)域,正是廣泛閱讀滋養(yǎng)了他犀利的洞察與多維的表達(dá)。對(duì)于文藝創(chuàng)作者而言,博覽群書(shū)如同打開(kāi)一扇扇世界的窗口,讓思維的根系扎得更深,汲取不同文化的養(yǎng)分,從而避免創(chuàng)作的狹隘與重復(fù)。
沈從文則從另一角度提出:“一本好書(shū),應(yīng)當(dāng)是一面鏡子,照見(jiàn)自己,也照見(jiàn)眾生。”在他看來(lái),閱讀不僅是知識(shí)的積累,更是心靈的對(duì)話與自我的審視。他的《邊城》等作品之所以充滿人性溫度與鄉(xiāng)土深情,離不開(kāi)他對(duì)生活細(xì)致入微的觀察,而這種觀察力往往通過(guò)閱讀經(jīng)典得以錘煉。文藝創(chuàng)作離不開(kāi)對(duì)人性深度的挖掘,而深度閱讀正是喚醒創(chuàng)作者內(nèi)在共鳴、理解復(fù)雜世相的鑰匙。
莫言曾幽默而深刻地說(shuō):“讀書(shū)少,寫(xiě)作就容易‘營(yíng)養(yǎng)不良’。”他以魔幻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手法融合鄉(xiāng)土敘事,其背后是對(duì)中外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的大量涉獵與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。從《聊齋志異》到馬爾克斯,莫言的閱讀經(jīng)驗(yàn)證明,創(chuàng)作上的創(chuàng)新常源于對(duì)不同文本的咀嚼與重構(gòu)。閱讀讓作家在傳統(tǒng)的土壤中長(zhǎng)出新的枝芽,在借鑒中形成獨(dú)特的語(yǔ)言風(fēng)格與敘事結(jié)構(gòu)。
王安憶則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閱讀是一種沉默的交談,它教會(huì)你耐心。”在她看來(lái),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尤其是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,需要作者擁有沉潛與堅(jiān)持的耐力。通過(guò)閱讀經(jīng)典作品,創(chuàng)作者不僅能學(xué)習(xí)謀篇布局的技巧,更能體悟文字背后的時(shí)間感與歷史厚重感。她的《長(zhǎng)恨歌》等作品對(duì)城市與人物命運(yùn)的綿密書(shū)寫(xiě),正是這種“耐心”的藝術(shù)體現(xiàn)。
余華的觀點(diǎn)更為直接:“讀書(shū)是為了活著,寫(xiě)作也是為了活著。”他將閱讀與創(chuàng)作提升到生命體驗(yàn)的高度。在《活著》等作品中,余華用簡(jiǎn)約而有力的筆觸刻畫(huà)苦難與堅(jiān)韌,這種力量部分源自他對(duì)卡夫卡、福克納等作家的閱讀消化——讀書(shū)讓他理解如何用文學(xué)承載生命的重量,而創(chuàng)作則成為他回應(yīng)存在的方式。
這些作家的閱讀觀雖各有側(cè)重,但共同指向一個(gè)核心:閱讀是文藝創(chuàng)作的源頭活水。它拓展認(rèn)知的邊界,淬煉思想的鋒芒,滋養(yǎng)情感的厚度,最終融入筆下的每一個(gè)字符。在信息泛濫的今天,這些箴言猶如清泉,提醒著每一位創(chuàng)作者:真正的創(chuàng)新從不憑空而來(lái),而是在浩瀚書(shū)海中揚(yáng)帆,抵達(dá)屬于自己的文學(xué)彼岸。
因此,無(wú)論是初執(zhí)筆的新人,還是久經(jīng)沙場(chǎng)的作家,都應(yīng)當(dāng)時(shí)時(shí)回望這些智語(yǔ)——在書(shū)頁(yè)翻動(dòng)聲中,尋找靈感的不竭之泉,在字里行間,鑄就屬于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文藝豐碑。